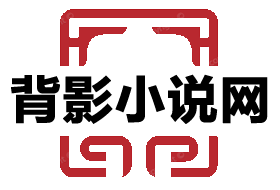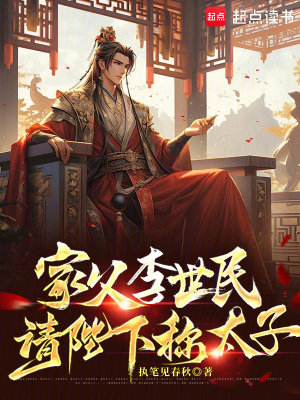第448章:以万国而养大唐
秋夜的风卷着西市的喧嚣穿过小巷,李义府坐在陋室的案前,无意识地敲打着那本磨卷了边的《农桑司实务纪要》。
三天前,他在酒肆听稽查司的小吏闲聊朝堂议事,那些碎片般的议论此刻仍在耳边盘旋,像无数根针扎着他的思绪。
“房相说要扩粮仓、疏漕运,可江南的粮运到关中,三成在路上就霉了,储得再多有什么用?”
“长孙尚书提农技考核,可新式农具到了乡野,百姓不会用还是白搭,去年下发的《农桑要术》,我老家县令都当废纸垫桌脚。”
“魏公要清查隐田,听着解气,可那些豪强哪个没后台?真要动起来,怕是朝堂先乱了。”
“褚卿的耐旱豆是好,可试种要等三年,今年关中的粮价都涨了,等得起吗?”
小吏们的闲言碎语,戳中了所有建议的软肋。
李义府灌了口冷茶,茶水顺着喉咙滑下,却压不住心头的烦躁。
他铺开纸笔,把几位大臣的主张一条条列出来,又逐条划掉。
房玄龄的储运是节流,解决不了开源的根本。
长孙无忌的农技是慢功,救不了眼前的粮荒。
魏征的抑兼并是险招,稍有不慎就会动摇新政根基。
褚遂良的新种是远谋,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“都在田亩里打转,可田亩就这么多,天旱了、涝了,一年的收成就没了。”
李义府喃喃自语,将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。
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照亮案上摊开的《大唐舆图》,中原的州县密密麻麻标着“歉收”“粮价涨”,而西域、天竺的方向却一片空白,只淡淡写着“胡商往来”。
这几天,他几乎没合眼。
白天跑去劝学馆听讲,晚上蹲在西市的粮行外,看胡商的驼队把一袋袋青稞、稻米卸下来,转眼就被粮商高价收走。
有次他忍不住拉住一个粟特商人问:“你们故乡的粮多吗?”
商人笑着拍他的肩膀:“多!多得能喂骆驼,就是运到长安太贵,还要给沿途部族交钱。”
“交钱……”李义府猛地站起身,在狭小的屋子里踱来踱去。
他想起当年随晋王李治巡视边地,那些部族首领见了唐军就谄媚送礼,见了商队就拦路抢劫。
想起百炼司的工匠说“新造的火炮能轰塌石墙”,边军将领私下说“有这东西,西域诸国不敢炸刺”。
一个念头隐隐冒出来,却又模糊不清。
他翻出压在箱底的《边军武备录》,那是他托旧部抄来的密册,上面记着“火炮射程三里,可破城防”“火铳百人齐射,可退千骑”。
划过“西域诸国畏火器甚”几个字,他忽然停住脚步。
为什么一定要跟外邦好好做买卖?为什么不能用更硬的手段让他们乖乖送粮?
这个想法让他浑身一震,既兴奋又不安。
他走到铜镜前,看着里面那个穿着洗发白襕衫的自己,眼眶深陷,鬓角甚至有了白发。
四年的失意磨掉了他的浮躁,却磨出了更冷的锋芒。
“温和的法子老臣们都想遍了,可太子要的是解决问题,不是体面。”
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冷笑:“他们不敢想的,才是我的机会。”
他重新铺开宣纸,笔尖悬在半空,手却在发抖。
如果只谈通商,必定淹没在众臣的策论里;可要是提“用火炮逼粮”,会不会被斥为“穷兵黩武”?
他想起太子推行新政时的果决。
为了修水泥官道,敢发行“基建债券”。
为了查贪腐,敢设“稽查司”直接查六部。
这位太子从来不怕手段激进,只怕没有实效。
“缺粮是死结,温和的解不开,就得用狠劲。”李义府咬了咬牙,将《边军武备录》与《西域商路图》并排铺开。
月光下,图上的商路像一条条血管,而军镇的位置恰如心脏,火器就是让血液流向大唐的动力。
他提笔写下“以军威驭万国”几个字,墨迹透过纸背,仿佛带着硝烟的味道。
窗外的风更紧了,吹得油灯忽明忽暗,映着他眼中跳动的野心。
李义府猛地一拍案几,笔尖重重落在纸上:“对!就是这样——他们怕什么,就用什么逼他们;他们要什么,就用什么钓他们!”
困扰多日的迷雾彻底散开,他知道,自己找到那个能让太子眼前一亮的策论了。这一次,他不谈仓储,不谈农技,不谈田亩,只谈刀枪与掌控,谈如何让万国的粮食,像潮水一样涌入大唐的粮仓。
李义府提笔写下新标题:《论以军威驭万国,固粮仓安大唐疏》,每一字都像裹着铁砂。
“太子殿下新政虽盛,然粮食之困根在‘产能有限、外粮难稳’。中原田亩亩产已至极限,而西域、天竺、波斯诸国多有粮谷盈余,却因畏我之心不足、贪利之念过盛,常以‘粮价暴涨’‘路途险阻’为由克扣。臣以为,欲取外邦之粮,需先亮大唐之刃。”
“百炼司新造火炮射程三里,火铳可洞铁甲,此乃慑服外邦之利器。请太子殿下令边军在伊吾、龟兹等商路要地增筑‘火器军镇’,每镇配火炮十门、火铳五百,由实务科进士掌军械调度。”
“凡附属国入贡,必令其亲眼观火炮演练,使其知大唐之威不可犯。”
“若有国敢拖欠粮赋,先断其丝绸、铁器贸易;仍不从,则遣军镇火器营‘巡边’,迫其献粮赎罪,一炮轰碎其王城一角,胜过千封盟约。”
写到此处,李义府眼中闪过狠厉。他太清楚外邦的本性,当年随晋王接触边事时便知,这些部族畏威不畏德,唯有拳头硬,才能让他们乖乖听话。
“凡大唐附属国,需按人口、亩产设‘年贡粮额’:天竺诸国岁输稻米十万石,西域诸部岁输青稞五万石,波斯以东岁输耐旱麦三万石,由朝廷派‘粮赋监’驻其王城,直接督粮。”
“粮赋监掌‘生杀权’:若该国丰年欠粮,可暂记其账,抵次年贸易税;若灾年仍敢藏粮,则由粮赋监联名军镇,奏请殿下派兵‘助其平乱’——实则抄没其粮仓,以儆效尤。”
他特意在“粮赋监”旁注:“多选实务科出身、懂农技者任之,既督粮,又‘教其新种’,恩威并施,使其不敢反。”
这既是控制手段,也是向太子表功,他懂实务,能任此职。
“光靠打不行,需恩威并施。许附属国以粮换物:每输粮百石,可换蜀锦十匹、铁器五件,或免除其商队关税三成;若能超额输粮,则赐其国王‘大唐荣誉将军’头衔,允许其子入长安劝学馆就读。”
“凡拖欠粮赋三次者,削其附属国资格,断一切贸易;凡勾结马匪劫粮者,直接派火器军镇‘清剿’,将其王城改为大唐粮仓——让万国皆知,与大唐做粮生意,只能赚,不能赖。”
李义府放下笔,案上的策论墨迹未干,却已透着一股血腥味。
这不是温和的通商策,是赤裸裸的军事掠夺,却被他包装成“固粮仓、安大唐”的良策。
他太了解李承乾,这位太子重实效,只要能解决粮食问题,手段激进些又何妨?
策论结尾,李义府添上一笔,锋芒毕露:“臣知此策看似酷烈,然乱世用重典,缺粮之年需铁腕。贸易是‘软绳’,军威是‘硬锁’,唯有软硬兼施,才能让万国之粮如江河归海,涌入大唐粮仓。”
“臣四年间留心边军火器、外邦粮产,愿往西域粮赋监效力,亲掌督粮之职。”
“若能用火炮轰开一条输粮之路,纵粉身碎骨,亦无怨无悔,为殿下固粮仓,为大唐安万民,此乃臣之愿也。”
最后一句写得情真意切,却掩不住字里行间的野心。
他要的哪里是“粮赋监”之职,他要的是借这个由头,重掌权力,让那些轻视他的人看看,他李义府的刀,从未钝过。
窗外的月光照进陋室,照亮策论上“火炮”“火铳”“军镇”等字眼,像一地碎刀。
李义府将策论折好,塞进怀中,青衫下的胸膛剧烈起伏。
这一次,他赌的不是太子重实务,而是太子需要一个够狠、够敢的人,去做那些老臣们不敢做的脏活。
西市的晨钟再次敲响时,李义府提着策论走向皇城司,脚步踏在青石板上,像战鼓在擂。
他知道,这封染着刀光的策论,要么让他万劫不复,要么让他重回权力的中心。
而他,赌得起。
也只能赌。
——
门下省。
贞观二十四年秋末的午后。
负责接收文书的主事王敬之漫不经心地接过卷宗,看清封皮上“前晋王长史、著作佐郎李义府”的落款时,手里的茶盏差点摔在案上。
“李义府?”
他失声低呼,引来周围同僚的侧目。
“那个夺嫡之争里的‘智囊’?他不是早被闲置了吗,怎么还会上策论?”
门下省掌政令审核,每日流转的文书数以百计,可“李义府”这个名字太过特殊。
四年前玄武门后,晋王李治的属官尽数被贬,李义府更是被视为“潜在隐患”,虽未获罪,却成了朝堂上的敏感人物。主事们围拢过来,看着卷宗上“实务策论”的标识,面面相觑。
“打开看看吧,按规矩,只要是实务策论,都得登记初审。”
资历最深的员外郎张柬之沉声道,指尖在封皮上顿了顿。
“好歹是明经科出身,或许真有见地。”
王敬之小心翼翼地拆开卷宗,展开策论的瞬间,脸上的惊讶渐渐变成错愕,最后化为掩饰不住的惶恐。
他越读越快,指尖都在发抖,读到“以火炮轰其壁垒”“抄没其粮仓以儆效尤”时,猛地合上策论,声音发紧:“这……这哪是策论,简直是战书!他竟主张用火炮逼附属国输粮,还要设‘粮赋监’掌生杀权,这也太激进了!”
周围的官员纷纷传阅,一时间门下省的值房里鸦雀无声,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。
有人倒吸冷气:“让边军火器营‘巡边’逼粮?这要是激起外邦叛乱,谁担得起责任?”
也有人皱眉:“话虽难听,可他说的是实话——西域诸国确实欺软怕硬,去年商队被劫了三回,朝廷也没严惩。”
张柬之捧着策论,眉头紧锁。
他为官多年,见惯了温和的民生策论,像这样字里行间带着刀光的奏疏,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李义府的文字尖锐狠辣,直指“通商不足以稳粮源”,主张“以军威为盾,贸易为饵”,甚至列出了具体的火器配置、粮赋额度,连如何“恩威并施”都写得清清楚楚,绝非空泛的狂言。
“可他是李义府啊。”
王敬之忧心忡忡。
“夺嫡之争时他名声太臭,太子殿下会信他吗?再说这策论主张动武,万一触怒殿下,咱们这些呈递的人会不会受牵连?”
这话戳中了众人的顾虑。门下省虽有审核之权,却也怕担责任。
一个失势的长史,提出如此激进的主张,若是扣上“挑拨邦交”“穷兵黩武”的帽子,谁也不敢担保自己能脱干系。
有人提议:“要不……压下来?就说‘内容不合实务’,退回去便是。”
张柬之摇了摇头:“太子殿下最恨‘因人事废言’,若是压下,将来被查出来,咱们才真要担责任。”
他沉吟片刻,又道:“再者,这策论虽狠,却也直指朝堂太子殿下提出的粮食之问,不可压。”
官员们再次争论起来,有人担心“激化矛盾”,有人觉得“值得一试”,值房里的气氛越发凝重。
最后张柬之拍板:“按规矩办。咱们在审核意见里注明‘策论主张激进,涉及边军调度需审慎’,然后密封上呈。至于采不采纳,由太子殿下定夺。”
夕阳西下时,李义府的策论被装进特制的木盒,由门下省的内侍捧着,一路送往东宫。
值房里的官员们望着内侍远去的背影,仍心有余悸。
这封来自失意长史的策论,像一块烫手的烙铁,不知会在东宫激起怎样的波澜。
而李义府此刻正蹲在西市的酒肆外,看着西市的繁华热闹。